长征,是红军九死一生的突围征程。
在接二连三的绝地与险境中,红军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他们面对数倍于自己的敌人,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共进行了380余次战斗,攻占700多座县城,牺牲了营以上干部多达430余人,共击溃国民党军数百个团,期间共经过14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大河,走过荒草地,翻过雪山,行程约二万五千里,最终在陕北扎根,开始打出了新天地,开辟了新的革命征程。
长征,也是共产党人自我修复的一次心灵之旅,他们重新找到了指路明灯—毛泽东。
自1933年1月“临时中央局”在上海无法立足,“临时中央局”的领导层,陆续迁往他们一直认为“路线错误”的苏区后,一场最为严重的路线斗争,就如暴风雨一样来临了。这场斗争结果是,左倾错误思想大肆蔓延,党风独断专行,使得缔造中央苏区与红军的毛泽东,受到了长时间的排挤,闲赋无事近三年(其实,他在临时中央局的领导层未到前,就被早他们闲赋了一年多)。
不仅如此,党内、军中、政府中,凡带有“毛泽东”思想路线的各级党、政、军领导者,几乎都得到了他们的“关照”,不再受到重用。以至于,中央苏区,在他们这一帮并不真正懂苏区,也不是缔造苏区的留洋派们的瞎指挥、乱指挥下,最终给苏区带来了灭顶之灾,直接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军迫不得已离开自己的根据地,开始了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生死征程。
幸好,在长征至暗时刻,红军终于重新认清了形势,重新审视了毛泽东,并将扭转乾坤的重任落到了他的身上,使得红军一次一次地避免了即将倾覆的命运。从通道转兵,到挥师贵州,到力拒打鼓新场,再到四渡赤水,与血与火,生与死的狭缝中转道,无不映证了红军重新选择的正确。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全军上下,全面接受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心甘情愿去执行他的命令,却并不是一帆风顺,一蹴而就、一步到位的,而是经历了一次次斗争、一场场风波,最终才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来说:“他们硬是要用血的代价与教训才能接受正确的意见。”
这场风波犹为独特,如果说以前的斗争大多来自于领导层之间的思想分歧与排挤的话,这一场风波的肇始,却是第一次来自于红军将领,这是以前所从来没有过的。
那就是林彪提出的“换帅”风波。正因此林彪吵着要“换帅”,还差点酿成了军中哗变。中共中央不得已,只得在事发的策源地会理,于1935年5月12日召开四川凉山会理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展示出的卓越的军事思想与战略战法,最终使得让全军上下,尤其是林彪等心服口服。
为了完整阐明这场风波的前后,我将从两个方面进行剖析,重点通过透析会理会议中,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是如何进一步得到确立和巩固的,从而威震三军,军心巩固。
一、“遵义会议”之后“会理会议”之前发生了什么?
二、为什么说“会理会议”之后毛泽东的政治地位得到巩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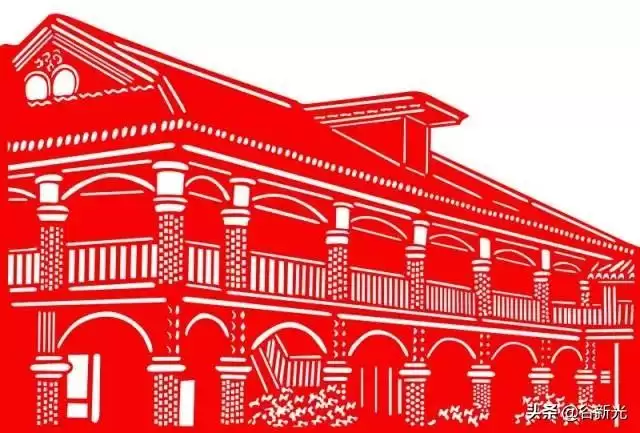
一、“遵义会议”之后“会理会议”之前发生了什么
遵义会议是红军长征中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1935年1月15日在贵州遵义召开。背景是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情况下,为了纠正博古、李德等“左”倾领导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而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遵义会议的召开,使得红军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作出了极为正确的选择,扭转了命运。遵义会议不仅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决定了由周恩来、朱德负责军事,周恩来为下最后决心的负责人,实际上取消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而且,最重要的是增选了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并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从后来的胜利转战奠定了基础。
遵义会议后,红军面貌开始大为改观,开始了一系列的漂亮征战,如二战娄山关、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等,还有审时度势、闪烁着智慧的打鼓新场之争,当然期间也经过了土城之役的无奈、鲁班场迫于战争需要而不得不打的表面失利之局,但对于红军而言,更正如毛泽东在二战娄山关后,写下的豪迈之作《忆秦娥·娄山关》中所表现的那样: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雄关漫道,迈步从头越。的确,红军正轻装收拾旧心情,征程万里,重新出发。所以,遵义会议以来,整体的战略意图正在逐步实现。
直到会理会议召开前,即遵义会议后近四个月的期间里,红军又于接连召开了鸡鸣三省会议、扎西会议、白沙会议,期间还经历了扎西整编。
可以说,是在通过这几次会议后,才真正、全面确立了毛泽东的军事领导地位。虽然,文件上的正式地位还要等到后来的“沙窝会议”,即“沙窝换帅”后才真正确立。
但至此,毛泽东的地位,已经从遵义会议“受到肯定”、鸡鸣三省会议成为“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扎西会议“以负党中央总的责任的张闻天和红军实际上最高领导的毛泽东互相配合,领导全党全军的新格局”、再到白沙会议“转变战略格局,开启四渡赤水的”序幕(决定二渡赤水)。
应该说,此时的毛泽东成为了红军不二领袖地位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至少,军事地位上已经明确。但他要争取全军上下广大指挥员,一致的认同,事实上,还需要一个过程,所以造成这种原因,无外乎以下三点:
第一点:毛泽东作为战争中走出来的革命领袖,是需要一场胜利接着一场胜利来奠定他的领袖地位的,所以全体上下整体接受他,也是有一个过程的。
正如周恩来1949年在中华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所作报告《学习毛泽东》时所说的,“决不要把毛泽东看成一个偶然的,天生的、神秘的、无法学习的领袖”,因为,“如果这样,我们承认我们的领袖就成了空谈。既然是谁也不能学习,那么毛泽东不就被大家孤立起来了吗?我们不就把毛泽东当成一个孤立的神了吗?那是封建社会、资产阶级社会所宣传的领袖”。
而毛泽东之所以高明,就在于他“是从人民当中生长出来的,是跟中国人民血肉相连的,是跟中国的大地、中国的社会密切相关的,是从中国近百年来和‘五四’以来的革命运动、多少年革命历史的经验教训中产生的人民领袖”。
充分说明这一点的案例,就是体现在打鼓新场之争上。

1935年3月10日,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万急”电报向中革军委建议:“野战军应向打鼓新场前进,消灭驻在西安寨、打鼓新场、三重堰之敌。”当时驻扎在打鼓新场一带的敌人,是国民党追剿军王家烈纵队(黔军)。
朱德认为:打鼓新场是黔北首镇,又是通往毕节的要塞,黔军比国民党中央军好打,打开打鼓新场有利于中央红军拓展川滇黔边根据地(扎西会议决定创建川滇黔边根据地)基础。他的意见其实也是绝大多数人的意见,主张打。
而只有毛泽东一个人主张不打。他还在云南威信县境内时,就已经构思好了要把滇军调到贵州腹地来,绕个大圈子把中央红军带出蒋介石大包围圈套小包围圈的绝境,北渡长江(金沙江)去川西北会合红四方面军,创建新根据地的战略计划。他的理由有两方面:
1、红军经过长途奔袭,特别是遵义战役后,队伍虽然稍稍恢复了元气,但综合力量还比较薄弱,且我军处境孤立,缺少外援;
2、军委二局戴镜元截获了敌方向遵义调动部队的电令,国民党中央军、川军、滇军正从四面八方向遵义、鸭溪、枫香、打鼓新场压来,蒋介石也很看重那打鼓新场这个地方,认为它是“共军西窜必经之地”,敌我形势十分严峻,如果贸然攻打,将会与滇军正面对垒,不能打固守之敌,部队受损不值得,应该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最后他作出判断:敌人100多个团的兵力,已对我军摆下南北夹击的阵势,如果此刻急于进攻打鼓新场,红军将有全军覆灭的危险。
但打与不打,当时的毛泽东个人的威望还不足以抗衡所有人,即使他以上任不足一个星期的前敌司令部政委的身份辞职不干的气话来威胁,也无济于事,甚至还被人当即以“少数应该服从多数,不干就不干!”的气话直顶了回去。
“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亦犹未悔”。最后,若不是怀有巨大历史使命感的毛泽东,在不计个人荣誉得失的情况下,连夜说服了周恩来,并于第二天会议上,又与周恩来一起说服了全体参会人员,才使得红军又一次避免了全军覆灭的危险。
从这一场打鼓新场风波中,我们完全可以看出,此时毛泽东的个人威望并未达到领袖群能的地位,而是通过随后的鲁班场之战失利的局面,才反面证明了毛泽东的高瞻远瞩和深谋远虑,从而逐步为毛泽东日后成为“新的三人军事小组”成员,真正掌握红军军事指挥权作了必要的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第二点:左倾错误思想依然存在,他们也还在党内把持着各个重要岗位,在一旦出现红军被动战地时,就开始散布谣言,与抱怨、消极作战思想沆瀣一气,动摇着军心。
如遵义会议结束后,博古虽被取消了领导军委工作的权力,但仍在党内负总责,还有凯丰等诸位大员党内地位一如以前。
当土城之役没有取得战前设想结果后,左倾教条主义与宗派主义思想又开始蠢蠢欲动,不甘心失败,对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后指挥红军机动作战本来就不服气,种种怪腔怪调盛行,“说什么毛泽东打仗也不过如此”等等,包括以后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他们又会推波助澜,散布毛泽东指挥不行了,要求撤换领导。此种思想盛行,在大敌当前的时期,自乱军心是对红军极不不利的。
第三点:也是核心因素,因时陷危局,军情无儿戏,不是课堂教学生,让全体指战员一下子全体明晰领袖的军事策略,是很难的,所以军队为什么要有一切听从上级指挥,不打折扣贯彻,恐怕在危亡时期意义更为重要。
为了确保红军战略意图的实现,在传达总的战略战术方针时,往往只直接告诉作战方向,没有任何解释,前后行动也不会有太多补充意图,当像红军长征这种极端的不利战窘出现时,各级指战员理解上的能力有限、听从上级指挥意念不强时,就会产生自我妄断上级的战略意图,从面出现了消极作战、抱怨、对抗等情形。
正因如此,林彪虽作为当时的红一军团长,高级指挥员,毛泽东麾下最为器重的战将,他居然也对这位他一直以来崇敬的领袖,产生了不信任感,认为他的战略战术出现了问题。这不正常,也正常。

说正常,是因为战场绝地,自红军长征以来,一直就没有摆脱过这种逃跑挨打的窘境,全军上下,各级指战友,除了决策层,又得不到红军真正的战略意图,战略只能贯彻执行,但执行又是如此之难度,下级反弹压力,所以部队的基层也开始出现了怨言与消极应战的情绪,尚属情理之中。
甚至,在一些中央和红军领导中,也出现了一股反对毛泽东军事指挥的倾向。他们认为,虽然在毛泽东和中革军委指挥下,红军由被动变为主动,甩掉了数十万敌军的重围,顺利地渡过金沙江,但红军行军时走了“弓背路”,搞得部队很疲劳,这样下去迟早也会把部队拖垮。
说不正常,就是林彪作为如此高级别的军事首长,常年来一直在毛泽东的军事影响之下,深受毛泽东信任与器重,怎就一下子跟着起哄,突然如此不理解了呢?有情绪就只能自己克制、消化,否则一旦真要把它实际地组织起来,就会惹出大问题。
林彪用通过一顿电话、一封电报,吵着嚷着要“换帅”,还一度差点激起了“战场哗变”,因这时的广大指战员皆因为不明情况而怨声载道,所以他的这一鼓噪,影响极坏。同时,此事,还从另一侧面也反映出,长期以来,离开了毛泽东正确指挥的红军队伍,在贯彻执行战略方针上,在领会上层战略意图上,各级指战员思想大有松懈。
林彪带着片面的军事思想,一直埋怨地说,我们尽走“弓背路”,要求走“弓弦”,走捷径。甚至说:“这样会把部队拖垮的,像这样领导指挥还行!?”
一渡赤水以后的第二天,即1935年1月30日,他和聂荣臻致电朱德:右纵队(由红一、红九军团和军委第二、第三梯队及干部团上干队组成)自西渡赤水后,部队走小路爬高山绕道太多,沿途群众极少,无粮食补给,只能吃稀粥,且受追敌侧击,建议经古蔺向永宁方向前进。4月23日,当部队向云南进军时,他又和聂荣臻致电朱德:“对目前行动,建议……须尽速脱离周、吴、孙(周浑元、吴奇伟、孙渡,当时分别任国民党“追剿”军第二路军第二、第一、第三纵队司令)而力求消灭万师(国民党“追剿”军第二路军第二纵队第十三师万耀煌部),如条件不利时,则应力求迅速超过万师,在万师以北即盘县、平彝以北活动。”电报还说:“须尽可能避免走‘弓背路’,而宁可对不大的敌人(守碉的)采取以一部监视,掩护主力取捷径通过的办法”向云南进军。这是目前我们发现的林彪提出“弓背路”说法最早的材料。
林彪视而不见:红军抢渡金沙江,以一昼夜行进100公里的速度,快速赶到金沙江边,并偷渡成功,牢固地控制了渡口,为大部队渡江创造了条件。通过广阔战场上的机动战,调动和打击敌人,并最终实现渡江北上,取得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重大胜利,是红军以少胜多,变被动为主动的光辉典范,也是毛泽东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的生动体现。
但林彪却固执地认为,强渡金沙江透支了部队,加深了对毛泽东及中革军委指挥上的不满情绪。尽管红军此时已摆脱了国民党军此阶段的围追堵截,但林彪却仍然认为四渡赤水以来路走多了。
他坚持认为部队行军应该走“弓弦”,取快捷方式。现在尽走“弓背”,会把部队拖垮。他说:“我们好比落在了敌人的口袋里,如果不声东击西,高度机动,如何出得来?”
终于,他来了个大爆发。于1935年5月11日,红一军团到达会理城外的大桥之后,林彪给彭德怀打电话,要求彭出来指挥。
不仅如此,林彪还写了一封给毛泽东、朱德和周恩来的长信。关于林信大意是,毛、朱、周随军主持大计,请彭德怀任前敌指挥,迅速北进与四方面军会合。”林彪把这封信给聂荣臻、左权、朱瑞和罗瑞卿传看了,并要求聂、左、朱、罗签名,但他们都表示拒绝。林彪就以个人名义将信发出。
万幸的是,林彪一手制造的“换帅”风波没有引起大的事变,虽然他的这种情绪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但由于大多数广指战员在一次又一次的战斗中,通过相互比较、前后比较,整体上认可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才能,也认为只有毛泽东才能将红军带出绝境,所以,在“换帅”风波上,他们都没有出来支持林彪,才使得红军避免了一次分裂危机。
而当“换帅”风波甚嚣尘上时,毛泽东从革命大局出发,一改过去王明、博古、李德那一套左倾做派,没有打击报复,而只是在风波的策源地召开一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让当事人林彪等都参加的会议,在会上,毛泽东抓住红军中存在的各种突出问题,从根本上统一红军思想的出发,解开了指战员们的心里疙瘩,为迎接今后更大的战争风暴作好思想上的准备与动员。
就这点没有打击报复而言,一直是毛泽东从军治政以来,最谨慎用力的地方,也是毛泽东与王明左倾思想上最大的不同,即党内同志以教育说服为主,而不是动辄杀伐。这显示了当时中央高层,尤其是毛泽东成熟的政治智慧与高屋建瓴的政治思想。

二、为什么说“会理会议”之后毛泽东的政治地位得到巩固
会理会议,于1935年5月12日,中共中央在四川省凉山州会理县城郊铁厂举行的扩大会议,这是一次在我看来,丝毫不亚于遵义会议的会议。
为什么这样评价呢?因为它不仅统一了中央红军的战略思想,进一步巩固了“遵义会议”的成果,是“遵义会议”精神的延续。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在此次会议之后,我们今天所颂扬的毛泽东军事思想才真正被红军各级指战员全面接受而折服。
会议上,主持张闻天作了有关形势的报告,并作了自我批评。周恩来、朱德等发言支持毛泽东,称赞他在危急的情况下,采取兜大圈子,机动作战的方针,四渡赤水,佯攻贵阳,威逼昆明,北渡金沙江,才使得红军摆脱了敌人的重兵包围。
最后,毛泽东向与会人员总结了红军四渡赤水抢渡金沙江的胜利,并完整阐明了他的运动战略的思想内涵。同时,他着重针对当前部队的思想情绪,进一步阐明了机动作战才能摆脱敌人重兵包围的作战方针,对林彪的所谓”走了弓背”的意见,和他给中央三人小组的信,作出了理性的批评,分析了大敌当前的形势下为什么不能走直路、走捷径的原因,又解析了为什么不能把每次作战意图向各级指挥员和盘托出的原因,使参会的军、政代表重新树立起了战略信念,从而统一了认识,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团结,巩固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坚持了正确的军事路线。
会议最后,还总结了遵义会议以来在川滇黔边实行大规模运动战的经验,讨论了渡江后的行动计划,决定立即北进,抢渡大渡河,向红四方面军靠拢的战略方针。
其实,单纯的战术思想是不能理解毛泽东的军事思想的。毛泽东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研究和指导中国革命战争,创造性地提出了“军事辩证法”概念,系统、深刻地阐明了关于战争和军队的一系列根本观点,揭示了军事领域矛盾运动的基本规律,总结提出了关于如何研究和指导战争的具有普遍意义的重要原则。
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思想,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理论精髓所在,它为正确地认识和指导战争,恰当地解决军事领域的各种矛盾,提供了基本的观点和方法。
虽然此时的毛泽东军事思想还在不断地发展与完善中,但其军事理论与框架已基本确立。在红军长征过程中,无不体现了他军事思想上的辩证关系。他的灵活机动、不受囿于战场形势、敢于险中取胜、轻装上阵、出奇不意、实事求是、声东击西等等军事艺术指挥原则,无不让人啧啧称奇。
长征中的扎西整编就是一出好戏,让人意想不到,又恰如其分。“二月里来到扎西,部队改编好整齐;发展川南游击队,扩大红军三千几……”这是后来陆定一、贾拓夫编写的《长征歌》中的真实写照。
1935年扎西会议后,红军开始整编。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当年毛泽东在井冈山进行革命斗争时,因为部队力量不够,为了虚张声势,把红军编为红四军,让人觉得红军很强大似的,不仅有四军,还有一军、二军、三军等。事实上这一招是当时是非常有用的。

今天,红军到了扎西,居然不再虚张声势,主动缩编,难道红军此时很强大吗?没有,但此时非彼时,井冈时期是据守,以逸待劳,居然声势很重要;此时是长征突围,机动灵活才是第一要义。部队损兵折将,不适时缩编,一则会助长官僚思想,能上不能下,二则会因编制太大,层次太多,上情下达,自然漫长,造成战场被动。
正是因为提前看到了部队组织上的大问题,整编是势在必行。
整编后的一个团兵力达2000多人,相当于整编前的一个师。为加强战斗力,除军委干部团外,全军整编为16个团。其中红一军团编为2个师6个团,其余各军团均取消师级编制,红三军团编为4个团,红五、红九军团各编为3个团。
在中央红军的战斗序列中,林彪指挥的红一军团战斗风格灵活多变,擅长运动战和伏击战;彭德怀指挥的红三军团擅长攻坚战,能打啃骨头的硬仗;红五军团原是冯玉祥的西北军队伍,于江西宁都起义加入红军,擅长打阻击战和担任后卫,军团长是起义将领董振堂;红九军团则擅长远程奔袭和游击战,军团长是马夫出身的传奇将领罗炳辉。
整编后的红军压缩了机关,充实了部队,战斗力大所提高。红军后来能在四渡赤水中,实施大踏步的机动作战,毛泽东提前进行的扎西整编是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环节。
红军扎西整编与秋收起义时期的三湾改编一样,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部队编制上的缩编,而是中央红军在军事路线和战略战术上的新起点,是第五次反“围剿”到遵义会议后,十多万红军战士用生命换来的经验,也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具体体现。
从扎西会议红军整编后,到毛泽东一生中最为得意的“四渡赤水”战争,无不体现了毛泽东军事斗争思想的新奇性、独特性。
今天的我们知道,一渡赤水被逼无奈,二渡赤水权宜之计,只有从三渡赤水开始,红军才开始把自己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三渡赤水起到了布置疑兵的目的,四渡赤水完成了声东击西的金蝉脱壳之计。三渡赤水和四渡赤水是连为一体,一气呵成的,三渡赤水是为了四渡赤水,四渡赤水是三渡赤水战略目的的达成。
其实,今天的我们应该理解,苟坝会议上毛泽东反对攻打打鼓新场开始,说明他思想上,对四渡赤水已经构思完毕,后面的行动,都是对这个战略的执行。所以从长征这些脍炙人口的战争案例来看,伴随着毛泽东一整套军事思想的日趋成熟,只要红军广大指战员全面执行他的命令,不打折扣,等待红军的就是,一个胜利接一个胜利。
所以,辩证而言,正是因为有了前因,毛泽东在整体战场对弈上,为身处绝境的红军摆脱了一系列的被动挨打局面,取得了一场又一场的战争胜利,那即使后来,发生了一些指战员消极应战、抱怨,甚至是要“换帅”的风波,绝大多数的广大指战员内心是透亮的,毛泽东的领袖地位是不能再动摇的,动摇就会付出巨大的代价,他的伟大的军事思想也是别人所不能比拟的,他的高瞻远瞩与运筹帷幄,正是红军的指路明灯、克敌制胜的法宝。
会理会议后,毛泽东,从此犹如红军的“定海神针”一样,肩负着红军重大的历史使命,雄关漫道,雪山草地,九死一生,带领着红军,走出绝境,迎接以后一个又一个风暴口的来临,并最终指挥这支队伍,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携手天下同胞,抵御外寇,解放全国,迈向了世界的中央。

参考资料:
1、长征史料与文献; 2、《长征史诗》;
2、《毛泽东传》; 4、《毛泽东军事思想》
5、《会理会议史料》; 6、《彭德怀回忆录》;
7、《聂荣臻回忆录》; 8、《李聚奎回忆录》;
9、网络相关史料的引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