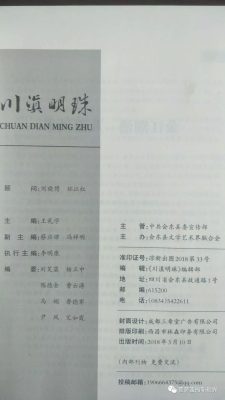近日,我收到了四川省凉山州会东县文联李主席《川滇明珠》创刊号,并担任其执行编辑。这是我的文字第一次出现在我家乡出版的第一本刊物上。我很荣幸也很高兴。我很高兴,因为我的荣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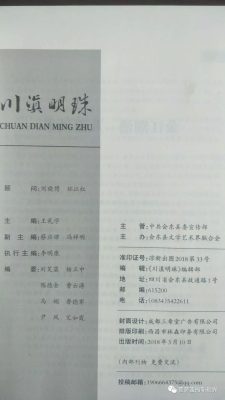
几个月前,李兄委托会东县政协原主席冯祥明向我逼稿,难得我与冯大哥的天地不老情,一贯懒散的我,从了,从微信扒了三篇喜剧写法的生活小品发过去。三篇文章分别是写头发衰落的《我型我秀“金箍咒”》、写牙痛的《我的牙将》和写咬伤舌头的《嚼舌根之战》。为什么要选这几篇嘻哈风格的小品?我美其名曰丰富刊物阅读内容,舒缓刊物阅读节奏。话虽然说得好听,但骗不了自己,懒病已让我欠下了不少文债书债歌债。

写作是个好事,以文会友的获得感绝不会输给以酒会友。开卷之处,一批新朋旧友迎面走来,尽管英雄各有各的出处,各有各的风采,但相聚在同一本书中,大家的人格和造型又都表现出了平等性和一致性。
不管你是领导还是下属,不管你是男女老少,不管你在故土或在天涯,大家都是一个方块字:字体一样,或黑或宋;字号一样,或大或小;字意一样,讲好会东故事,展示会东魅力,繁荣会东文化,憧憬会东理想。

见字如面,除了不认识的,唯一的新朋友是写创刊词的县委书记、县人大主任刘晓博同志,他上个月来重庆招商引资,短暂夜晤,但因在场人多,我们交流简短。在创刊词中,他从史地文等角度抒情言志,金沙江畔,一部钢琴吐露了自己豪迈的心声。
凉山文坛的多面手何万敏近年热衷驴行,田野调查式的采写凉山本地的历史地理,硕果累累,这次他到了万里长江第一滩探险,把头顶落石和脚下恶浪变成了坚实的文字,贡献了头条文章《走一回金沙江上“老君滩”》。万敏兄这样的做人做事做文的风格,让我坚信,我们发韧于二十多年前的友谊是坚实得可以靠起耍的。

《人民日报》原编委兼海外版总编辑詹国枢老师也写了一篇他41年前在会东参加高考的散文,写国写家,深情款款。他做《经济日报》副总编时,我去拜访过他。作为媒体高管和一代名记,他热情地为一个大学生小老乡热情沏茶拉家常,让我更坚定了一辈子都不装逼的做人信念。
会东藉老作家蔡应律前辈也为刊物贡献了纪实文学作品和对联。他是我父亲的学长,也是我后来在《凉山文学》做编辑时的作者和忘年交。我父亲初中毕业后因家庭成份高而无缘升学,我年少时他就希望儿子像蔡老师一样成为一名作家。我大学毕业后仅做了两年文学就改行做了新闻,不知算不算违背了先父的初心。

作者中还有我的初中同学赵海华,多年未见;还有我一见如故的朋友石兴普,他的热情似彝族人家的火塘,捂起是为了保护火种永不熄灭。翻到杂志封三时,我看见了大学学弟、县委副书记吉木尔依的照片,他正在为小学生们赠送礼品,古铜色的脸上绽放着笑容。学哲学的能笑出这个效果,是我这个学文学的没能想像到的。

除了社会的朋友,社会的历史也很迷人。《锦江支队:不可磨灭的序列号》的创刊号吸引了我一眼就看完了。文章中的许多当地历史名人都是我们从小就熟悉的。从支队司令员徐寅厚,到王龙云的三儿子龙春,再到回里苏少章,他们把我的家史、亲情史交织在一起,共同演绎了一页边疆史。晋江支队队长鲁烈士是我的叔叔。他的女儿陆春华姐姐去年给我发了一篇文章,说他希望写一篇关于晋江支队的文章。我不知道那是不是我的钢笔能到的地方?